小红书上,为什么这么多老师想辞职?
 本文配图来自《3年A班》
本文配图来自《3年A班》
六月底,中国学校的暑假前夕。
讲台上的粉笔一根根磨秃,家长群的提示音密集如骤雨。夏天已经抵达,教室里却仍在追赶试卷留下的空白。讲评、成绩、告别、总结接踵而至,校园节奏却并未因放假而变得轻松,反而有一种积压许久的情绪,在教师中缓缓浮出水面。
这种情绪不再只是隐秘的私人感受。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老师想辞职”“#教师抑郁”“#教书上头”正成为流量聚集地,一条条带着匿名与疲惫的笔记,在高频更新着同行们的心理刻度线。评论区里,不只有“理解老师”的家长,也有同行之间的互相确认:“我也是。”“你说出了我的感受。”
近几年来,每一个学期的末尾,几乎都成为情绪崩塌的高发期。睡眠障碍、条件反射、过度警觉、内在抽离、沉默攻击。这些原本属于临床诊断的术语,正在以碎片的方式嵌入教师的日常生活:有人在讲台上突然语塞,有人连续数周凌晨惊醒,也有人在办公室悄悄服药,再若无其事地走进教室。
教育部数据显示,全国有超过1885万名专任教师。这个庞大的职业群体,正在经历一场难以言说的心理危机。它没有突发事件作为引爆点,也未引起舆论喧哗,更像是一种持续性疼痛:不是被瞬间刺痛,而是被慢慢耗空。
过去三年,随着“双减”、课后服务、全覆盖督导、数字化监管等政策叠加,教师的“教育性劳动”正不断被“治理性任务”吞噬。他们成为应急响应人、信息记录员、舆情缓冲带、情绪调节器,乃至“第一责任人”。
在部分地区,一位教师每天的“非教学行为”被记录到分钟维度:几点到岗、发了几次通知、上传了多少材料、家校沟通是否留痕。讲课,反倒成了夹缝中的喘息。
在社交平台上,“教师抑郁”“教师焦虑”早已不再是讳莫如深的词汇。有人说,教师是新时代情绪债务的“结点人”。多方的情绪压力汇聚于此,而他们自己的出口,却从未真正建成。
讲台下的低语
在中国的大多数中小学,讲台的高度没有变,构造也没有变。只是,站在它后面的人,越来越沉默、疲惫了。
这种沉默,源自一种深层的耗竭。它不是崩溃,而是无法崩溃。在公共叙事中,教师仍被定义为“稳定者”“奉献者”,他们承载着大量象征意义,却很少拥有情绪表达的空间。
过去一学期,全国教师心理热线的接入频率持续走高,网络平台上,“长期应激”“班主任抑郁”等词条浏览量翻倍。社交平台上的匿名吐槽,像裂缝中渗出的水汽:“不是想死,只是不想醒来。”“我甚至不知道,我还在教书这件事里。”
在小红书、豆瓣等社区,越来越多教师开始匿名写下自己的“教学体检报告”。与其说是发声,不如说是一种自救。他们说:“写出来不是为了被看见,而是不想再一个人扛。”
那些写下“想辞职”的人,并不一定真要离开,而是想问一句:教书这件事,还能不能不那么痛苦地维持下去。
一位心理咨询师说,如今很多教师在迟疑很久后才敢承认:“可能需要一点帮助。”在一次心理测评的开放题中,有人写道:“我已经没有能力应付下一个学生的情绪了。”
这些情绪的表现不是轰烈的,而是持续的、碎片的。早醒、梦中监考、条件反射摸手机、对亲人缺乏耐心、对学生强作镇定。这些“高功能抑郁”的表现,被许多人称作“正常”。
有小学教师描述过这样一个瞬间:站在讲台上,突然发现不记得刚才讲了什么,只是机械地翻动课本,念出熟悉的话语,仿佛身体还在履行职责,而内在早已不在场。

在一个日益强调“流程可量化”“风险可控”“情绪可治理”的系统中,教师的心理状态似乎从未被视作“变量”。每一份延迟的管理指标、每一次“不要出事”的背后,都有人在悄悄承受。
在一场关于“情绪劳动”的讲座上,一位教育研究者指出:现代学校中,教师早已不只是教学者,更是信息上传者、风险预警者、秩序维稳者。职能不断扩张,情绪管理随之透支。
一位接受精神科诊断的离职教师曾写下自己的“症状日志”:清晨睁眼先想学生有无请假;白天会幻听;深夜无法入睡,脑中不断闪回家长训斥、学生情绪失控、领导责备的画面。她写道:“我焦虑两公里外、两小时后的任何事,极度厌恶人生。”
在不少地区,教师还需完成“心理健康宣传”“安全讲评”等事务性工作。形式清晰,过程留痕,但教师是否真正疲惫,常常沉没于制度之外。
有教师写道:“每堂课开始前,我都会深呼吸五秒——不是为了学生,是为了提醒自己,还能站在这儿。”
裂缝埋在日常里
如果说过去我们常将教师心理困境归咎于“个体脆弱”,那么如今,它越来越像是被结构性力量制造出的结果。某种隐形的慢性压力,正在悄然穿透讲台与生活之间的界限。
最直接的体现,是职责边界的持续外扩。教师从“知识传递者”变为“全流程守护者”:授课、家校沟通、心理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处置、责任记录,几乎无所不包。
一位县城高中教师说,他从清晨五点半陪跑操开始,深夜批改作文结束,除授课外,还需查寝、写材料、跟进心理排查。连如厕都需“排进节奏里”。
他曾因课堂劝阻学生玩手机而遭粗口回怼,事后仍需在会议上“作经验分享”,反思“如何避免冲突升级”。他说:“凡事不能出事,出了事就有人负责。”而“负责”的意思,就是流程完备、留痕齐全。
更根本的变化,是角色身份的漂移。教师不再被视为“专业工作者”,而更像一个“微型治理节点”。他们是学生波动的“第一知情者”,也是最容易成为“第一责任人”的人。
在小红书上,“教师心理”相关话题浏览量超过了1000万。一些教师会对手机产生条件反射:“改作业到11点,家长突然发60秒语音轰炸”,“放假也心悸手抖,总感觉手机在震”。在长期应激状态下,一些人出现了一连串的躯体反应:肩颈硬得像铁板,肠胃动不动抗议,明明很困但凌晨三点自动睁眼,开始出现“粉笔手抖症”“监考幻听症”,看到学生奔跑就心慌,对家人没耐心却对家长笑脸相迎,路过学校围墙会加速心跳。
大量吐槽汇聚于凌晨时分,以片段化的形式泄出压抑:
“我承认我病了,但在学生面前要优雅、稳定,所以更抑郁。”
“惊恐发作,住院一个月,现在看见低年级学生都会应激。”
“每天回家向自己孩子发脾气,给老公发脾气,想离家出走。”
“半夜心脏痛,痛得厉害,莫名其妙想上天台。”
“在深圳干了四年初中老师,抑郁了三年。一上班就焦虑,每天有气无力。”
“工作两年,觉得自己的人生完蛋了。”
“每天脑海都闪现一跃而下的念头。路边的狗都能吠几下,我却不敢辞职。”
“我梦见自己爬上教学楼,一跃而下。但梦醒,还得批作业。”

也许问题从来不是教师越来越脆弱,而是这个职业,越来越不允许他们表达脆弱。
谁来疏导老师?
心理教师,本应是学校中安放情绪的角色。但在现实中,他们往往被推入一个悖论:既要调解他人情绪,又难以照顾自己的状态;被视为“安全阀”,却缺乏真正发挥作用的时间、空间与支持。
青青是一位心理学硕士,2021年起任教于深圳一所九年一贯制公立学校,怀着“能做点什么”的愿望进入系统。学校有三名心理老师。从四年级开始,每个年级每周一节心理课,八年级为隔周一次。除此之外,她还要负责延时服务、社团带队、“宣传周”活动、行政会议。每周留给学生个体咨询的时间,不足四小时。
有些被班主任推荐来的学生,并非有心理困扰,而是“不听话”“不合群”“不够乖”。心理室逐渐成为“行为矫正”的一部分,而非理解与陪伴的空间。
青青试图坚持专业:建立信任、保持倾听。但在高密度事务节奏与制度性考核压力下,她感到“真诚也会变形”。“你渴望倾听,却要在15分钟内归结问题类型;你想陪伴,却还得打分、写材料、归档。”
一次,一位有自伤记录的学生向她连续求助三周。但由于心理室“排满”,她只能约到“下周三下午第二节”。那名学生最终没有来。
在不少学校,心理教师还要配合各类督查工作:“心理健康宣传”要附图文、家校反馈;“节前心理排查”需形成台账;学生心理档案成为“校安平台”审查指标。真正的咨询被压缩为流程中的一个附属环节。
青青曾在社交平台写下这样一句话:“我不是在陪孩子面对自己,而是在帮系统排查不确定性。”这句话后来被她删除。担心被误读,也怕“被看见”。
这份迟疑,并非她一个人的心情。青青和很多老师聊过,她发现,那些外表冷静、沉默应对的同行,常常会经历这样的时刻:站在讲台上,看着学生却像隔着一层玻璃,内心毫无波澜;学生举手,只想敷衍几句;学生哭了,心理上甚至没有反应,反而觉得“矫情”。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是一种典型的自我保护机制,就像大脑启动了节能模式。在长期情绪透支之后,不自觉地与他人拉开距离,用标签代替名字,用流程替代交流。“这是空杯子理论的反面,”青青说,“他们不是不给,而是已经没有水可倒。”
更深层的困境是“专业孤岛”。在深圳,尚有同行交流、外部督导。但在一些县区小学,心理教师往往是唯一岗位,缺少反馈机制、也无同行共情。在处理高压事件时,他们只能独自承担。
青青曾自费参加线上心理督导,也尝试组建远程支持小组,帮助偏远地区教师“讲讲这周在被什么折磨”。她说:“专业性不强,但有人听着,本身就能喘口气。”
一位曾在精神卫生中心实习的心理老师说:“学校配的不是心理支持系统,是风险责任人。出了事,谁签字谁疏导,责任就落在哪。”心理支持在某些语境中,悄然异化为“风险前置”的管理机制。教师、学生、家长的情绪问题被导入心理室,而那个“窗口”背后的支撑体系,却未真正建成。
后来,青青试着减少“改变一切”的冲动,把精力放在那些力所能及的细节上。她说:“真正让人走出低谷的,未必是心理老师说了什么,而是他们曾在一个空间里,被允许安静地做回自己。”
那个“我”去哪了?
“我现在讲课像在演,陪家长像在演,写材料像在演。每天做很多事,但好像都不是我在做。”一位教师这样描述自己的日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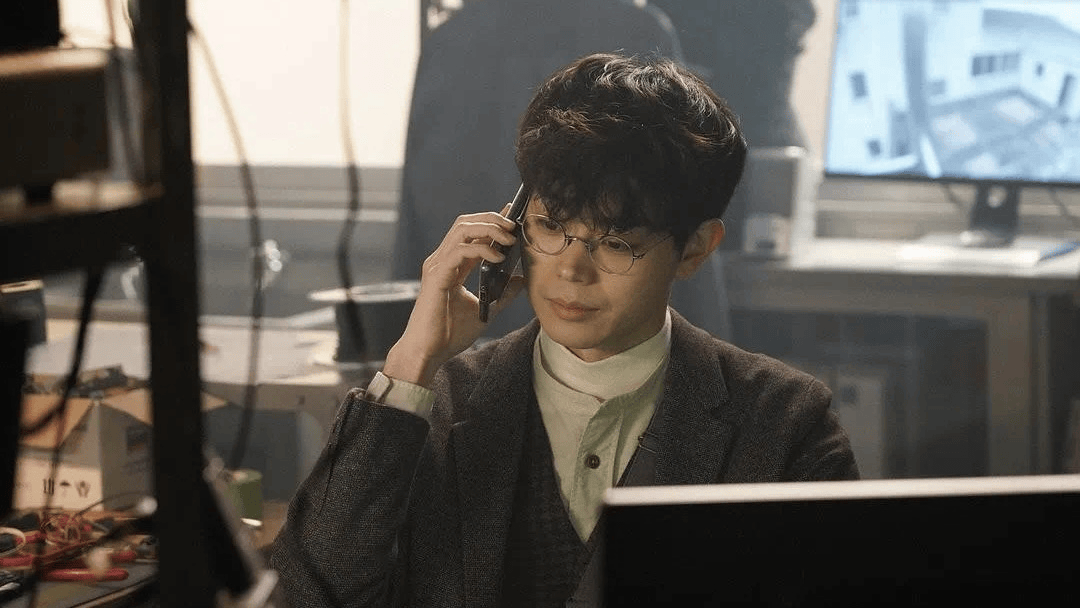
越来越多教师在谈到表达时,不是说“我不想说”,而是“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说”。他们的沉默更像是一种情绪的绕行:避免误读,也避免反弹。当说出每一句话都必须对照角色、规避风险、符合气氛,一个人便不再真正说话,而只是在扮演说话的人。
语言的收缩意味着转向。有研究者称之为“自我建构的表达策略”:不是压抑,而是折叠;不是无话,而是不再把话说满。真实的表达,被转移进朋友圈的一句歌词、匿名帖的一张配图、课堂里对一首古诗的强调。他们没有沉默,只是把表达交给了“隐喻”。
这背后是一整套心理调控机制。
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认为,个体主体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在权力结构中“被制造”出的特定身份。教师在这种结构下,逐步“合身”为系统所需的形象:得体、克制、稳定、有力。他们的“我是谁”,让位于“我该成为什么样子”。
艾芙·塞吉维克对“羞耻机制”的阐释,更指向了这种转变的深处:羞耻并非源于错误,而是源于一种持续的、自我比照的察觉,即意识到“我不该是这个样子”。它不是一次情绪崩塌,而是一种日常的、结构化的自我调节方式,使人自动剪除那些“不合身份”的感受与欲望。
在“必须负责”的逻辑下,表达变成了自我压缩与角色表演,那个未经格式化的“我”,也就渐渐退场了。很多教师因此进入某种“心理抽离”状态:上课如常,下课失语,面对学生时反应迟钝,对教学事务失去意义感。他们仍站在讲台上,却像被拧紧的发条,只在程序中运转。这不是冷漠,而是一种被规训出的钝感,一种情绪长期不能外泄后的麻木保护。
在持续的规训中,教师的情绪表达被层层收束。他们不再是可以犹豫、迟疑、表达不适的个体,而是被塑造成一种合乎制度的“形象”,外在完整,内里隐匿。
但沉默并不意味着空无。那些微弱、不成系统、不被记录的语言,仍在缝隙中留下某种最低限度的回响。正如巴赫金所说:“所有言语都是在回应之中诞生的。”哪怕在高速转动的教育飞轮之下,人与人之间仍在努力维持一种朴素的理解:一次默契的点头,一句课后的叮咛,一个不经意的停顿。
语言退场的地方,也可能是另一种开始的预示。或许,教育真正依赖的,从来不是宏大的话语,而是那些在沉默中仍不放弃连接的意愿。
那些未被撤回的微光
教育系统是一组缓慢转动的齿轮。它不因个体的意志而改变,也难以轻易停下。在它的缝隙之间,仍有人试图留下微光。
有教师在延时服务后多留十分钟,不讲试卷,只跟学生聊聊“今天最开心的事”;有班主任在群发通知后加上一句“也请家长们照顾好自己”;还有心理教师,每周抽一个中午陪学生绕操场走一圈,不测评,不记档。

他们不是为了改变什么,而是为了抵消一点什么。
青青仍在深圳那所学校任职。她已不再期待能用一节课“解决”一个问题,更在意的是学生离开心理室前,脸上肌肉是否放松了一点。有时甚至不交谈,只在教室门口点点头,算是一种默契的照面。
她还在尝试为其他心理教师建立一个小型线上“同侪支持组”,每月一次语音会议,无主题,无输出。“只是彼此确认还在,还在这个行业里,还在讲,还在听,还没有离开。”
还有人做得更小。在寒假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一位小学语文老师在黑板右下角写了两个字:“慢点。”孩子们问什么意思,她说:“就是让你写字慢一点,呼吸也慢一点。”在一个强调速度、留痕、流程、达标的系统中,它们像是制度表格边缘贴上的一张手写便签,提醒彼此:我们还有一点未被格式化的部分。
依然有人不以为然,他们说,那些喊累的人只是“卷不动”罢了。他们自觉适应良好,也小有斩获。他们说:“哪有那么多崩溃?干得好就不累。”然而,如果一个系统只容得下“干得好”的人,只允许那些不会喊疼的声音被听见,那它最终留下的,就不会是一群完整的人,而是一群被磨合得刚好合身的齿轮。
老郑是北方一所县城重点高中的语文老师,教书已十年。他说,最初讲李白,是仰着头念“天生我材必有用”,后来低着头说“抽刀断水水更流”,现在干脆不说了。
他所在学校以军事化管理出名:天未亮就带学生跑操,晚上查寝,几乎无休。他带三个班,每周有三个早自习和四个晚自习,四次集体备课。校领导在大会上反复强调要“狠抓教学”“狠抓成绩”“狠抓安全”,他说自己有时梦里也在狠抓。
“学生一届一届能走,老师走不了。像被困在一个闭环里打转,有上不完的高中。”有一次,凌晨两点,他打开手机日历,给自己设了个提醒:“坚持到下届毕业。”
不是所有努力都能改变什么,但一些教师仍在做着那些细小的动作,哪怕只是在一张表格之外,多留一秒钟的停顿,多看一个学生的神色。他们未曾离开这个系统,也不奢望挣脱它。但在它的缝隙中,他们尽力让自己没有变成它的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