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考上高中的小镇三姐妹:在乡村振兴的缝隙中点亮人生
常婉莹/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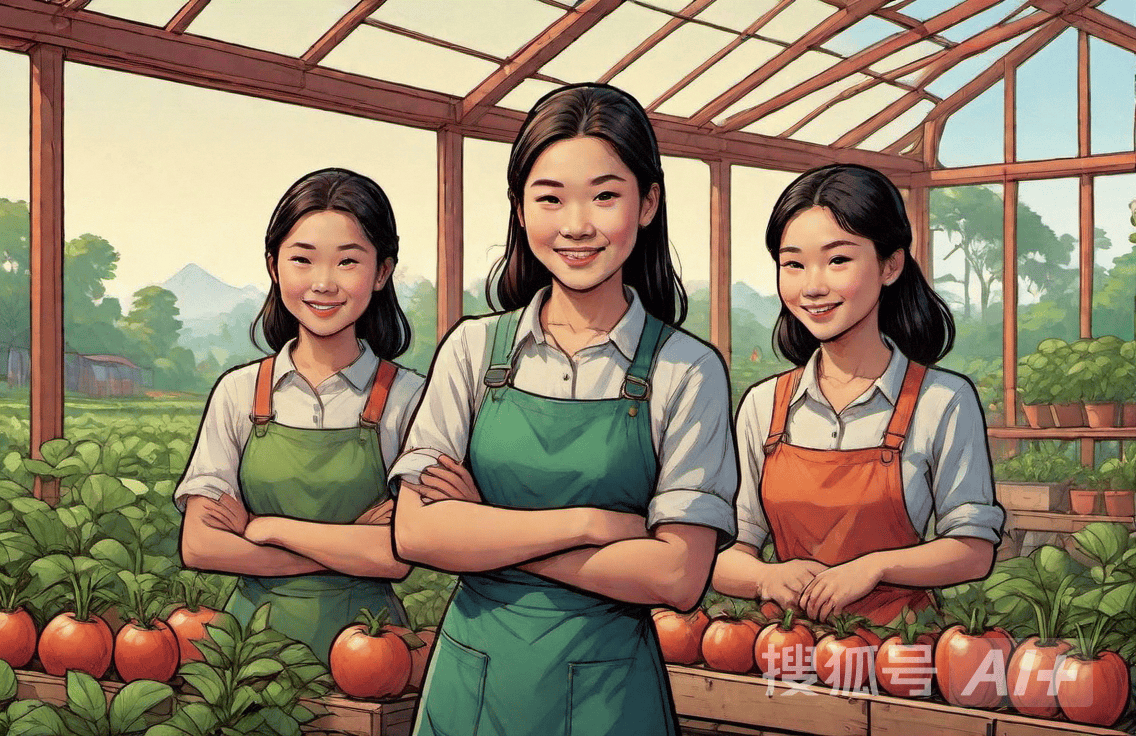
今年的高考帷幕已徐徐落下,对于考生和考生家长来说,这无怪乎是一次凤凰涅槃,让人惊心动魄。
高考——就业——结婚生子,这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的理想目标和人生规划。面对高考独木桥,一些考生并未能如愿,有的甚至在初中、高中就夭折了。夭折就失败了吗?就是失败的人生吗?无数铁的事实证明,这样的结论肯定是否定的。
有业内学者指出,教育改革的终极目标不是“取消考试”,而是构建“多元成功”的价值坐标系。对个体而言,应允许有人深耕学术,有人精研技艺,有人在艺术领域绽放光彩。如芬兰教育倡导的“每个孩子都是冠军”,评价标准从“筛选淘汰”转向“潜能激发”。
六月的帝都,酷热难耐。于是与朋友相约,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然而,这次旅行却意外引发了我对创业就业的一些思考……
汽车飞奔一个小时左右,下车发现已到京郊,一个大大的月亮门,上面写着“XX村蔬菜种植基地”。
走进去,似来到大棚的世界,数不清的遍地大棚,上面都挡上了遮阳布,我们随便走进一处,只见绿植满满,灯光柔和,只有一条小路可过人,看来这里的土地已充分利用。
听见有人进来,从小屋里闪出三名女生,都是20多岁的年龄,青春、朝气,活力十足!
她们说,刚干完活,今天的豆角已经运走,另一个女生抢着说“说不定现在已上了谁家的餐桌!”
看来她们很有成就感:
每天凌晨三点半她们就开始摘豆角,5点钟有专人来装车,6点钟保证装进老百姓的菜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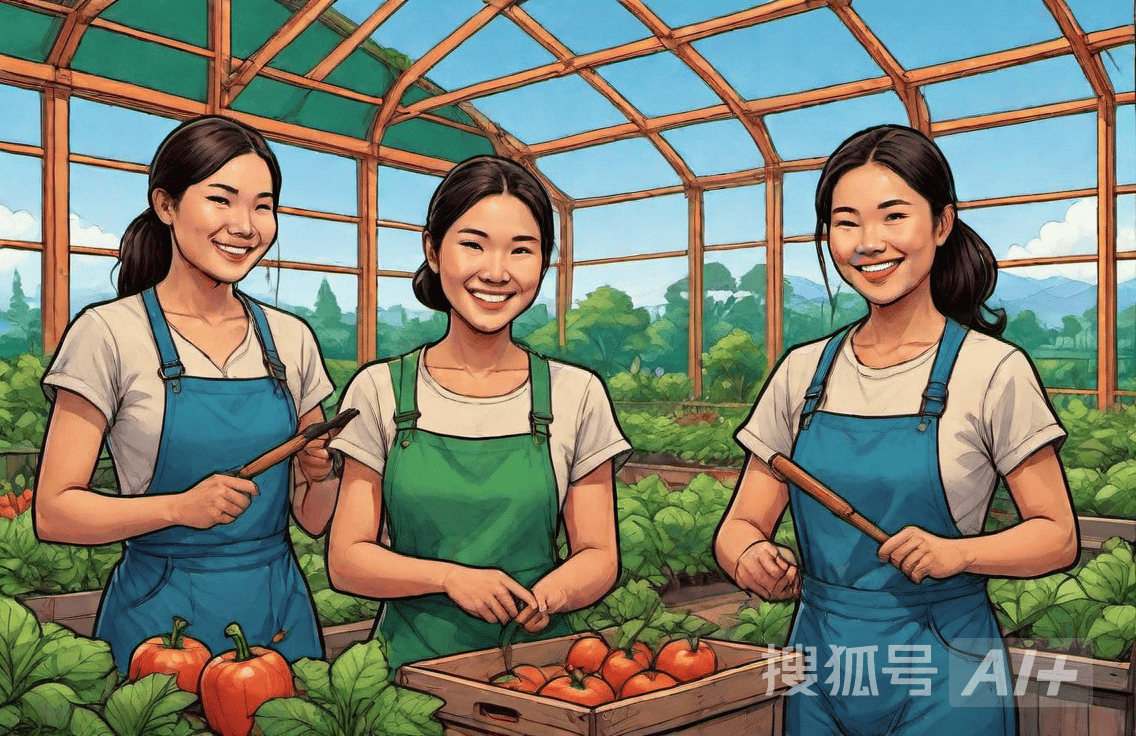
她们从屋里拿出几条细长的板凳,让我们坐下,开始介绍大棚的特色与种植情况,看来她们受过培训,讲起来轻车熟路……
这是很开朗的三位女生,恨不得把自己的经历全部倾述,她们说,别人都太忙,没人愿意听我们说,我们的经历能写一本小说。
大棚内温度表指向26度,空气清新,略带泥土味,我们真的做好了听的准备。
下面是三位女生的叙述:
我们三人来自乡下,同一个村,同班同学,都是初中毕业,因为沒考上高中,三人决定共闯天下。
家长告诉我们,学点真本领,挣钱自己花,家里的日子能维持,你们三人千万别拆帮,有事告诉家。
那年我们都16岁,离家后酷似流浪世界。我们处处小心,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见到大城市,在一个偏远的地方,看见一个招商广告,为了吃住有着落,马上找到那地方,是一个服装厂。
那家正招人,考了一下缝纫机操作,我们都会,又培训三天,就正式上岗了。
从此我们过上了月月领工资的日子,学会了上银行存款,学会了管理自已的账户,这样的日子持续不到两年,来了新冠疫情,我们暂回家休息。
2023年4月,当我们再兴致勃勃回厂时,发现工厂已转让,安上了自动化生产线,我们每人拿到了1000元离岗费,当天就沒人管吃住了,别提当时我们心中多么恐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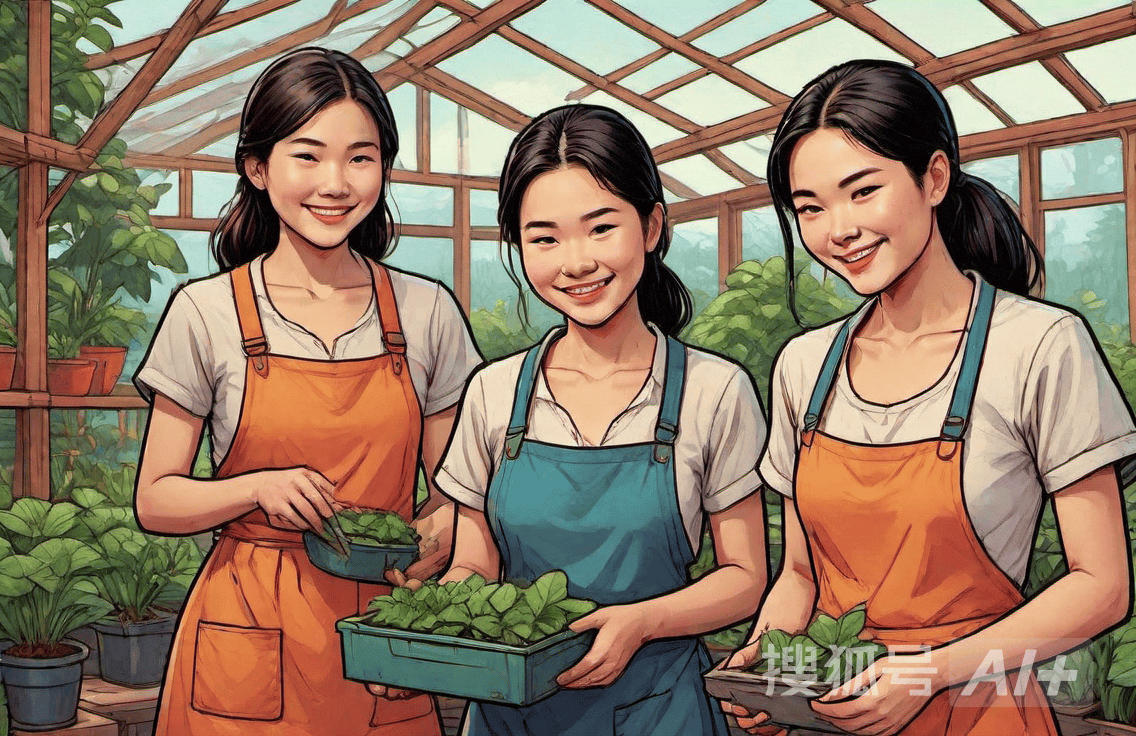
中午,我们在小摊上各吃了一碗刀削面,别无选择,只有互相鼓励,互相壮胆,口里说着天无绝人之路,开始了没谱的生活。
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租一个小柴房,只能晚上住3个人,白天呆不了,又闷又热,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不去想冬天冷时还住哪里。
我们把白天的任务命为“考察出路”,从此像脱疆的野马,混进了大城市的每个角落,看热闹,赏风景,也趁机长一些见识,想到回乡时,还能讲一讲新鲜事,让人羡慕,也挺开心。
现在与你们敞开说,这找工作的一年半时间,我们几乎撞得头破血流,考察了不少工作,都以不适合而告终。
我们每天坐着公交车(地铁太贵,我们不敢多花钱),到处跑,总觉得啥都有机会,见识了不少职业,走过了许多弯路。
说起来,不怕你们笑话,有时我们的心气还挺高,或者叫不知天高地厚吧,我们还去听过一次“AI招聘会”,还听过一次“芯片制作的要求”课,三个初中生,大模大样地坐在课堂上,与大学生混在一起,当我们发现啥也听不懂时,我们心中的世界,与人家讲的内容,中间有断层,我们两次都悄悄的离开了这种地方,自称“又踩了雷”,也恨自已当年没好好学习。
随后我们总结了教训,别总想高口味,还是看低层经济,很快,我们买了一个带玻璃罩的手推车,是专为做煎饼用的,求邻居帮忙,社区同意,有个小地方,人口出入多,让我们卖烤肠、豆浆、自制煎饼等。

于是,又一次磨拳擦掌,进货,备料,练手艺,忙得不亦乐乎,三个换班,忙时两人,闲时一人,备班人可休息,随时支援……
我们干劲十足不到三个月,每天晚上收工前,我们都做三份大点的煎饼,放两个鸡蛋,火腿等,到屋后洗手先吃饱,烤肠随便吃,都不记账,两个月下来,发现没挣钱,收支差不多,于是又没有干劲,到第三个月,就不干了,移动手推煎饼车,也低价卖出,白忙活了三个多月……
由于我们不会精打细算,也不擅总结自已的不足,结论只是“这项工作不适合我们”,便为自已开脱了。
摸摸自已兜里的钱,越来越少,我们有一个共识,不能再做自已拿钱,有成本的买卖,想起“零成本创业”这个词。
我们紧迫感十足,不过几天,先找到一个“出租伴娘〞的公司,职业要求一栏写的是:
“长相一般,不抢风头,有服务意识,没有社恐症。”
我们讨论一下,共同认为,这个工作不行。因为我们条件太一般,在大庭广众之下,不会显示自我,表情一定木讷,变成人们笑料,还是先有自知之明吧,决定不去应聘。
12月份,我们一起接了一个群众演员的活,很快,拍电影的新奇感退去之后,群众演员体会的全是苦和累。
我们拍“路人甲,路人乙”都不够资格,我们叫“布景路人中的一员〞。
就是走几趟,但收入少,提前到,无限等,不自由,又冷又饿,体会一次也就足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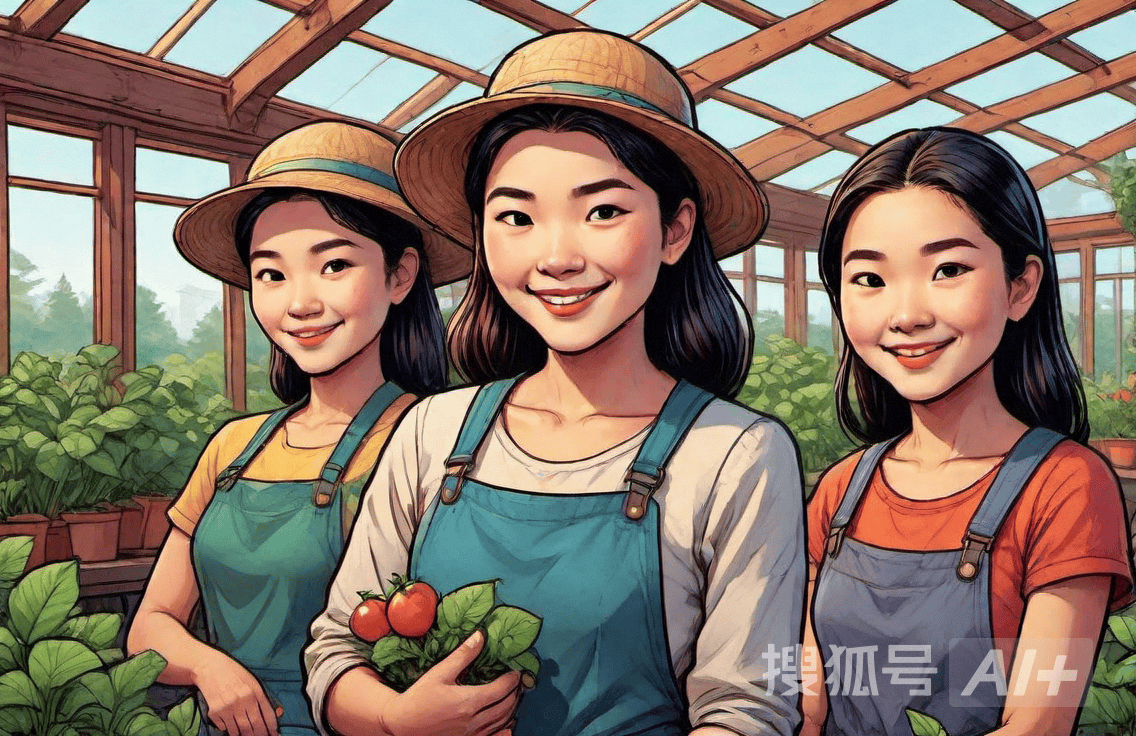
在我们第一次听课时,还遇见一位男生,他告诉我们几句话,至今还记得,他说,他本是名校学建筑专业的,他毕业那年,正赶上国家有一个“房子只住不炒”的理念,他决定再学一个人工智能。
他说转行的第一原则是,带着自己的优势,迁移到趋势向上的行业。
我们明白,话是大学生说的,应该与我们无关,因为距离太远,想够也够不着。
按我们的水平,找适合我们的工作就对了,我们只知道,世界这么大,应该谁都有路走。
在折腾了一年多,见识了几个工种后,我们已经没钱了,日子开始紧巴巴,但恐慌感也不像开始那么强了,我们学会了省吃俭用,也能耐受了生活的种种磨砺,明白了失败可以从头再来……
我们慢慢发现,对普通人来说,脚踏实地的做好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已经很了不起了。
这一年半,我们跟着别人卷来卷去,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们,每个乡镇区都有主管就业的地方,可以问问专项负责人,他们的信息很多且很可靠。
果然,我们当天就落实了工作。
我们自身的条件是,身体好,能干活,年轻,有积极性,大棚里这些活,当年在家都干过。

我们看中这里不交房费,不收水电费,有住的地方,有做饭的㕑房,收入比原来的服装厂还稳定,谁能不吃菜呢!
我们当天就签定合同,当天就搬过来了,落实一切,大功告成。
我们本以为她们的话结束了,但那个高个子女生又形象地比喻一下:
她抬起一棵豆角边缘爬过来的蔓说,你们看,蔓的生长与攀缘能力都很强,但它盲目的毛病也够呛,有时一条长蔓脱离了竹杆,绕不上去了,只有在空中颤抖着。
就像一个盲人摸不到扶手与拐杖,蔓的问题就是只知成长,不认方向,与我们开始失业时的乱闯一个样!
当时不知道各地都有扶持失业人员的机构,还有人专管,专事专办,有祥细的登记表,我们到这里就与到家一样了,边填表,边落实,边同意我们去报到,这该有多好!
三个女孩的一番话,让我们感动。这就是失业再就业的路。
如今正是毕业季,这三个女生的自救路曲曲折折,虽是大千世界中的一桩小事,但或许会给现实中尤其在创业路上的年轻人带来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