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部长推动“中高考改革”,北大教授儿子初高中两次辍学:是该救救孩子了
“我的母亲是北大教授,我辍了两次学。”
前段时间北京大学教授赵冬梅的演讲引发了全网热议,她的儿子出身北大教授家庭,却经历了厌学、休学,以及初高中两次辍学。
而最近,赵冬梅的儿子泱泱——佟浩然,也在演讲中,从他的视角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他说到:“上学和不上学都是不同的路,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两条路都要克服很多困难才能走到终点。”
而对于赵冬梅而言,一开始,她也不太能接受孩子不上学,几次想要将孩子重新送回学校,孩子去过大专、出国读过高中,但最后还是离开了学校。
陪儿子最终脱离学校教育这个轨道的过程中,她不断问自己:“我需要儿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最终,她找到了自己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对于仍在学校教育中内卷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以及我们的教育系统和环境,也提供了一些解法。
尤其是看到近日央视《焦点访谈》采访中,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提出要:
推动高考综合改革,加快探索推进均衡派位、登记备案等中考多元录取机制。将通过政策和制度的设计来淡化竞争,减少焦虑。
而如果环境改变,很多孩子的黄金那几年可能就不会浪费,就不会走上一条走不通的道路。

1
从厌学到初中辍学:
“学校的环境特别‘卷’”
泱泱选择辍学,早已有迹可循。
他认为这可能跟父母从小对他的“放养”教育有关:爸妈都是北大的大学教授,一个研究生物,一个研究历史,但他们在儿子身上的教育模式,却并不死板。
当别的孩子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而早早就提前学习小学阶段的知识时,泱泱每天一个人在外面玩到八、九点才回家。这让泱泱觉得自己有时挺“异类”的,当别人在玩命学习时,他甚至约不到一个可以一起出去玩的伙伴。
“我很贪玩,但学校的环境却又特别‘卷’。”
在这样的背景下,泱泱的学习成绩自然不好。而老师一般都不太欢迎成绩差的孩子。
当他和同学发生冲突时,老师也总是会偏袒成绩更好的学生,而不是成绩常年垫底的泱泱。
在小时候的他看来,说不上来哪儿不对,只知道自己怀着一种不适的感觉,直到初中,这种不适终于才在不断积累之下迎来了爆发。
初中时,因为中考的升学压力,学校的环境更加压抑。
周考、月考、小考、大考......学习的进度要往前赶,考试的次数也逐渐增多。考试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检测学习的成效,但在疯狂内卷的环境下,考试逐渐成了同学之间竞争、攀比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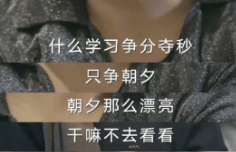
初入这个环境的泱泱,并没有一开始就摆烂、厌学,刚上初中的他,决心好好学,毕竟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没有人想甘于人后。
但从60分提到了70分,并不会有任何的正向反馈,在结果导向的教育评价体系里,考试只有100分和0分,要么是学霸,要么是学渣。
泱泱记得,老师常对他说:“你爸妈怎么生出你这样的孩子”。
“学霸父母孩子也得是学霸”——这样的观念始终压在泱泱的肩上,成绩差成了他的“原罪”,也让赵冬梅在老师面前感到羞愧。
但赵冬梅想,自己孩子成绩差,到底是哪里差?是谁规定的这个“差”?
在她看来,如果以过去的标准来看,泱泱绝对不算是个成绩差的孩子,每次考试,他的成绩都能维持在75分以上,偶尔还能考一百分。
只是因为在“优绩主义”盛行的今天,全班同学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只要不考高分和满分,都算是“成绩差”。

上学在泱泱这里逐渐成为一个背负着巨大心理压力的事情,“休学”这颗种子也一点一点地在他心里发芽。
起初,只是“装病”,让妈妈帮他请假,一次两次三次,直到不断请假成为一种心理负担,就像对上学积攒的负面情绪一样,请假的次数越多,返校的想法就越少。
没有哪一天就“正式”的选择休学,而是在一次请长假之后,泱泱就再也没有回过学校。
他把自己屋里的门锁起来,几乎不和父母见面。为了避免白天撞上,泱泱甚至把作息昼夜颠倒,天亮了就睡觉,等晚上父母睡了,再出门上厕所。一种若有若无的低气压,始终笼罩在他头上。
直到泱泱意识到自己已经“休学”时,他才把那口始终憋着的气呼了出去。就像攥了太久的沙子终于撒了手,那些日夜翻腾的纠结、自我拉扯,突然就跟着散了。
当然,他心里头也没因此亮堂起来,那份松快里总裹着层说不清的沉,算不上多舒坦,倒像是没底的空罐子,晃一晃,尽是发闷的回响。
他情绪的变化终究也瞒不过家人的眼睛,辍学这件事像根无形的线,一头牵着他心里的空落,另一头则缠成了父母心头解不开的结。

毕竟,要父母接受孩子的休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休学后的一年里,赵冬梅和丈夫、丈夫和泱泱总是发生争吵,赵冬梅一边要安慰儿子,安慰丈夫,还要安慰自己。
那段时间不仅是泱泱一个人的难熬,更是赵冬梅人生的至暗时刻,每次回家的时候,她都总是会莫名其妙的紧张。“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在里边究竟怎么想,他会做些什么事情,我完全没有把握。”
在走进小区楼的时候,赵冬梅的脑海里也会不断地预演,楼底下会不会聚集了一堆看热闹的人,或者那个楼底下有没有拉起警戒线。
泱泱把自己关在房间多少天,赵冬梅就提心吊胆了多少天。
无论是赵冬梅还是泱泱,那时的他们都陷入了无穷无尽的迷茫,泱泱的未来在哪里?眼前一片迷雾,他们似乎看不到终点。
2
辍学以后:
“我开始接纳孩子做一个普通人”
作为一个从小学习不用愁、成绩始终名列前茅的“学霸”,赵冬梅对学校教育抱有一种惯性,希望孩子走“读书”这条最安全、最简单的路。
因此,在赵冬梅和丈夫看来,再怎么样也得找一个学上。
一开始,赵冬梅通过投儿子所好、带他做手工,让儿子的情绪有所好转。好转后,她的第一反应是帮孩子补课、让孩子回学校,可回去后儿子考得差,厌学情绪又反复,最终初中辍学了。
后来,他们给泱泱找了一个大专的预科——一个常规之外的学校。

在大专里,没有为了成绩而内卷的同学,也没有为了分数而焦虑不安的氛围,泱泱在里面获得了在以前的学校从来没有得到过的自由。
每次回家,泱泱都会跟妈妈讲他的同学,讲自己正在读院长推荐的书。赵冬梅觉得那时的自己“心里乐开了花。”
“甚至在那里,我觉得儿子像‘学霸’了。”
但和所有家长一样,当孩子表现的“还可以”时,家长总是会觉得孩子“还能更可以”。于是一开始的“只要孩子开心快乐”慢慢被膨胀的欲望取代,从“厌学”情绪中好转之后,赵冬梅认为泱泱又可以重返学校了。
“大家应该听过普希金的那个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就像那个渔夫的老婆一样,对,我又加码了。”
在去美国进修一年时,赵冬梅想把儿子也带过去调整一下,重新回到高中,重新拾起那个沉寂已久的“大学梦”。
但美国的高中也很卷。泱泱每天早上起来去上学,因为听不懂语言,到了教室一坐就是一天。“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中国的学渣到了美国的高中,并不会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学霸。”
为了不辜负妈妈的信任,泱泱还是熬下来了,他艰难地把一次次考试都考及格。
但看着儿子明明不喜欢却仍要痛苦地去学的身影,赵冬梅不禁反问自己:“我到底需不需要他去再回到学校去?”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赵冬梅总是会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她想,学校教育并不是天经地义自古就有的,既然是后天建构的,为什么所有孩子都得走这一套呢?不走学校教育的道路,是不是也可以?

内心里隐约有一个答案告诉她,不上学,天并不会塌。那些因为离开学校而缺失的教育,或许在其他方面也能够得到补足。
例如赵冬梅逐渐发现了儿子身上的一个闪光点,当泱泱需要用到某种知识时,他会去主动地利用各种途径去找,而在赵冬梅看来,这是一个人很重要的学习能力,“我想这个本事可保他无虞”。

当她意识到这一点时,她明白,儿子确实不再需要重新回到学校去了,他能够养活自己,也可以活得很好。
于是,赵冬梅终于和儿子辍学这件事和解,她不在执着于送孩子回学校,“我接纳我的孩子做一个普通人”。
但她和儿子约定好:可以不上学,但必须接受自己没有大学文凭这件事。
赵冬梅和泱泱说,“你想好了,要你想谋求文凭,你就横下一条心,把苦吃下来,回去上学。但你说,咱不要这些了。你得保证:将来有一天,跟同龄人再坐在一个桌子上,你不能自卑。”
他们也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可以不上学,但不能不学习。
3
那些脱离轨道的脚步,
通往的是独一无二的风景
辍学后的泱泱也确实从未停止过学习:
他觉得编程很有意思,就去自学了编程;喜欢四驱车,就去汽修店里帮朋友修车改车;18岁时,他开始琢磨自学摄影,靠帮别人拍汽车活动的照片,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如今的泱泱,是一名摄影师,从摄影助理到正式入行成为一名专业摄影师,他用了三年。
那个曾经贪玩的孩子,如今可以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抱着几十斤的设备满场飞。
因为摄影这份工作如今给他的成就感,以及那种努力就能得到正反馈的收获,让他逐渐感受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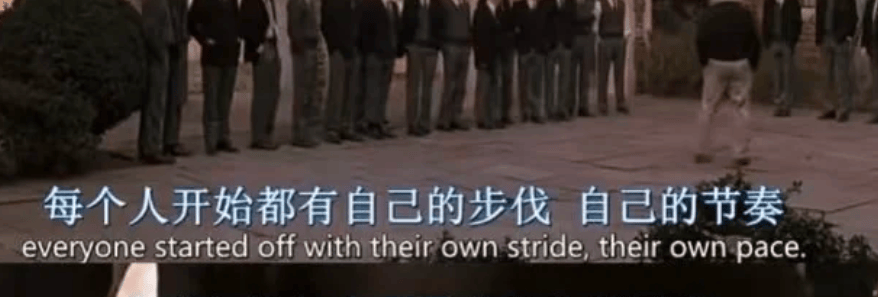
看着儿子在如今的工作中熠熠生辉,赵冬梅也不再纠结那段辍学的经历。
如今的赵冬梅认为,陪孩子走来的这一路,是孩子给她上了一课。
对于儿子被学校落在了身后,赵冬梅一直很自责,但她并没有觉得是自己和丈夫从小对泱泱“放养”式的教育让儿子脱轨,相反,她认为是她从小对儿子的关心不够,没有及时发现他和学校教育“格格不入”。
“我从17岁上北大就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所以对于北大以外的世界,包括小学、中学我都不太了解,因此我没有给我儿子足够的帮助。”
她不断反思,自己忽略了儿子在班级里始终是一个被忽视的角色,“我其实多少年以来,都不知道他的学上得那么痛苦。老实说我其实是到很后来才真正的理解了他”。
当赵冬梅再次想起儿子辍学的事,她才意识到,自己从前总以为儿子是因为学习不好才不愿去学校。
身为学霸的她和孩子爸爸都觉得,只要一家人拧成一股绳,逼孩子一把——“只要他用功,我们花一点时间搞一搞,我们就一定搞上去了。”
但他们都忽视了,儿子和学校教育的“不搭”,从来就不在于成绩好不好,而是在于他从内心里很难认同学校教育的选拔逻辑。
在疯狂内卷的竞争下,他很难从学习这件事情上获得正向的反馈和肯定,而对于一个从小就被父母告知要在乎自己的感受的孩子来说,这样的环境是难以忍受的,辍学也就成为了必然。

而对于为什么总是抱有一种路径依赖——认为学校教育能解决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所有难题,赵冬梅也慢慢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我归根结底对自己是不放心的,或者说我没有那么足够的信心。我仍然希望我付钱把他托付给学校,把他托付给另外一些以此为职业的人,把他托付给一个体制,走大家都走的路。”
可正是这种将孩子托付给体制的依赖,让她不由地往深处想:当我们默认沿着这条大家都走的路前行时,我们是否忽略了些什么?
赵冬梅进一步思考今天的学校教育——“当学校把语文数学英语这些知识排在第一位时,那些跟生命、生活有关的的常识和知识,却要等完成了全部的教育、进入社会之后才开始学习。”
而后者,对于一个人的生存和生活来说,也许更加重要。从这一点出发,去探寻学校教育之外的另一条路,似乎无可厚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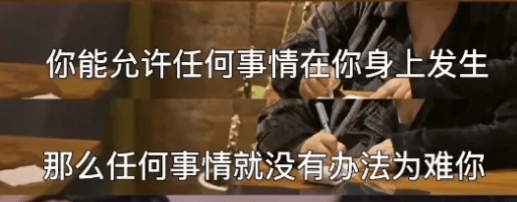
当然,赵冬梅和儿子的故事有一定的特殊性,泱泱之所以能够不断试错自己的人生,离不开父母对他的兜底。他自己也说到“放在一个普通的北漂家庭,你大概只能走最确定的那条路”。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今天通过他的故事去看到教育的另一面。很多孩子在学校里一直被贴上“学渣”的标签,这并不代表他们就一事无成。
我们总是人为地去给人生的每个阶段设置一个固定的目标,例如读书的目标考一个好成绩,而考好成绩的目标则是上一个好大学,似乎只要达成了,就算是“上岸”。
但正如赵冬梅后来所说的:“‘上岸’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历史是复杂的,生活也是复杂的。人生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的确,当我们在学校教育中去寻求一种确定的答案,每个人都沿着那条设定好的人生路径前行时,往往忽略了其实人生远不只一条路可以走。

我们总在追问“怎样才算成功”,却忘了成功本就该有千万种模样。当我们愿意放下对“标准答案”的执念,允许孩子带着自己的节奏慢慢成长时,才会发现——
那些看似偏离轨道的脚步,最终会通往属于每个人出独一无二的风景。而这,或许才是教育最温柔的底色。
参考资料:
[1]一席少年-上次我来一席的身份是北大教授,这次是一位辍学孩子的妈妈
[2]新世相-我妈是北大教授,我初中都没上完
[3]新世相-承认吧,“上岸”是个伪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