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人民的大学,不是教师的大学”辨

最近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提出一个命题:
(一所)大学是人民的大学,不是教师的大学。
他的愿意是,大学是承载历史使命的,所以大学的意志和天命也绝非为大学内部教师所能主宰的。
意思是:大学的主人是人民。
如果按照当下经济学的思路去理解,就是说,大学的真正校董是人民:是公办的嘛,国家投资和建设的,用广大纳税人的钱来建设的,等等。
这里不说金力主张文科消减是否正确,但说他这个论证思路、这个命题是否有问题,是否有bug。
金力这个命题其实包含着一个他自己可能也未必知道的猫腻,一个很隐蔽的猫腻——就是思维降级,或者说降维打击。
这种打击绝对冠冕堂皇,无可反驳,无懈可击,实则悖谬。
以历史学中最抽象的词“人民”为主语,排斥、拆解大学教师对于大学建设的建言、甚至决策建议之权,实为荒谬。

在“是A,不是B”,这种句型中,A和B最好是平行级别的概念。
比如说,这支笔是张三的,不是李四的。张三和李四,两个个体,就是平级的。我们理解起来很顺畅。
“钓鱼岛是中国的,不是日本的”理解起来也很顺畅。但要这样说,“钓鱼岛是中国的,不是全球国家共同体的”理解起来就很麻烦了,因为中国和全球国家共同体就不是在一个层次或级别上。
在金力的这个句子中,“人民”这个集体概念与“教师”这个集合概念,就是不对称的,不是在一个级别上的。
人民一般指“劳动人民”,在阶级社会它对应的就是“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决不属于或等于劳动人民,反之亦然;在社会主义社会勉强对应的是“领导力量”,但是我们需要这样理解:这个领导力量与人民之间不存在根本厉害冲突。
所以按照这种平级逻辑,金力的话应该是:复旦是人民的,不是统治阶级的或者说不是领导力量的。
但是后种说法,说起来和听起来怎么都感觉别扭,生活中没人会这么说,仿佛有“人民”就够了,“人民”就是一切,不必再在“人民”中抠出什么或为“人民”安排一个对立面。
因此,说“大学是人民的”,这句话不宜再跟什么了,不要再承接什么“不是什么”。
但假如有人偏要说,我要像金力校长那样,在肯定句中使用一个总体谓词,再在否定句中使用一个具体谓词,那样又如何呢?
情景一:
譬如一个生产队长说,这仓库里的粮食是生产队的,不是你张三的(张三是生产队里的一个成员)。张三一听哑口无言,但是他会说,里面有我的一份子啊!
我要领回我的那一份。
队长说,对不起,必须等交了公粮,扣除集体开支,才能领回“属于”你的那一部分。
这里生产队可以换成某个企业,任何一个类似的生产集体。
这里从属性个体并没有拿回他所有的部分,而是只是扣除后的那一属于他的小部分。
他其实被剥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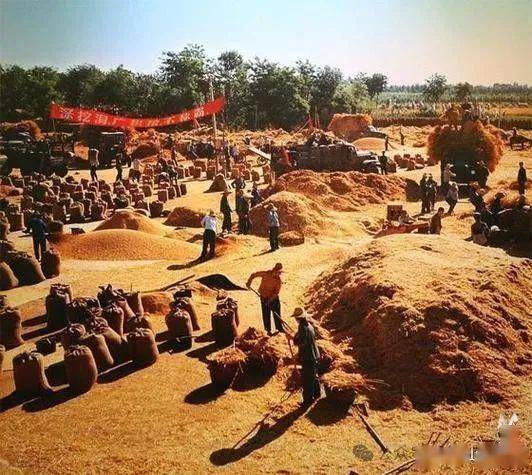
情景二:
某个邮电局员工对客户说:
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我不是为你服务的。
客户顽固地辩护说:
你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你必须为我服务。
二者完全是悖论,邮电局员工的意思是,为人民是总体,总体不等于个体。
客户的意思是,总体不是个体,但是总体包含个体。
客户被蔑视了。

情景三:
复旦校长说:大学是人民的大学。
A做了推论:大学是人民的大学,所以人民有权知道和介入大学发展决策全过程。
大学教师属于人民范畴,
所以大学教师有权知道和介入复旦发展决策全过程。
所以大学的文科教师也有权知道和介入复旦发展决策全过程。
所以,就这一点而言,复旦也是复旦教师的复旦,也是复旦文科教师的复旦。如果复旦文科教师都反对或绝大多数反对金力的任一倡议,他们是否有否决权呢?
按照上述推理,答案是肯定的。
至此,很清楚,在涉及经济利益的情况下,集体劳动所有制包含对个体劳动的征用;在涉及服务的情况下,集体概念往往成为服务打折扣的理由;而在涉及权利的情况下,集体概念可以直接成为抹杀从属性个体的权利的工具。
我们无法像阿多诺那样试图推翻“概念拜物教”,但是我们想指出,金力校长试图以人民的名义来论证复旦加强工科或交叉学科的改革思路是无效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给人这种印象,校长试图抹杀复旦教师对于学校改革发展的知情权、决策权、和参与权。这无论于发扬社会主义主人翁精神,还是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都是背道而驰的。而这也将极大地削弱他的论证力量。
一个认定“大学是人民的大学”的人,怎么会走到“反民主”的立场上去呢?
这恐怕恰恰是复旦大学、甚至金力本人需要反思的问题。
如果考虑到去年初夏一位台湾省夏姓学生对于复旦的愤怒与狂傲,而至今复旦对于他的来历(据推断他的父母可能某夏姓高官)讳莫如深,我们更加认为金力需要好好捋一捋人民概念。
他莫不会说“大学是人民的大学,不是公众的大学”了吧?

▲复旦大学校长金力,见南方周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