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哪就供到哪,那些“被忽视”的县城孩子

这些年,教育成了人们的必争之地,“鸡娃”“内卷”这些热门网络词汇背后,其实是无数父母对孩子未来的焦虑。
不过,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这股拼教育的劲头,到如今好像有点慢慢地变味了。
在大城市里,中学生们的生活,就像电视剧一样丰富多彩,这样那样的兴趣班,特长技能,他们路线是准备升入国内高校,或者干脆瞄准了海外的大学。
而与此同时,许许多多县城里的中学生,生活却完全是另一种画风。
这些孩子读完县城高中,然后呢?大多数都得走向社会、奔向各自的命运。这些县城高中生的梦想很简单,“我要去厂里挣第一笔钱”,“我要回家开个小店”。
再看他们的人生轨迹,就像一个圆,读完高中进了工厂,挣了钱,又回到了人生出发的地方,那个生养他们的小城或村子,然后成家生子。
这些孩子的身影很少出现在媒体报道里,但他们却是中国经济的隐形支柱。十几岁的年纪,他们进厂做工,把中国的“世界工厂”撑得稳稳的。
可是,尽管这个群体占据了全国中学生总人数一半以上的比例,关于他们的教育问题,对他们的关注,却少得让人心疼。而他们最后的学习堡垒——县城高中,正在一个被忽视的角落,悄悄凋零。
今天路sir要讲的这本书,聚焦的正是这个被人们忽略的群体——“县中的孩子们”。
作者林小英用一种真诚又不失犀利的笔触,把这群孩子拉回到大家的视野中。
他们没有华丽的履历,没有耀眼的起点,但他们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咱们社会的教育公平问题,甚至是城乡资源的分配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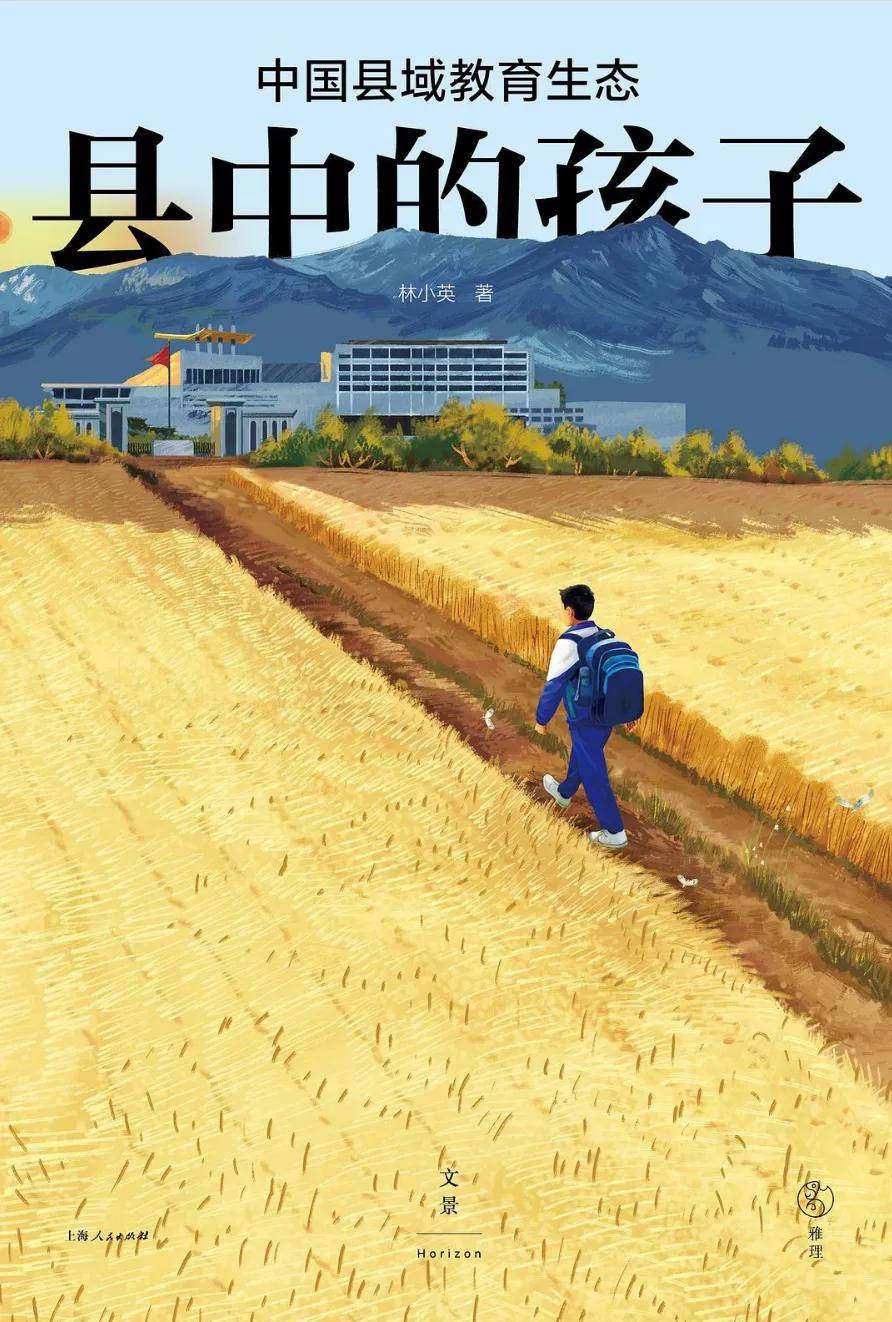
上海人民出版社
1.县城教育困境
在这本书里,林小英以P县为例。P县隶属于一个经济发达省份,虽说经济水平总体还不行,但因为地处山区,相比周边地区还是要落后一些。
十几年前,P县第一中学还是省级示范高中,是当地孩子心目中的“圣地”。可短短十几年时间,这所学校却一步一步走向了衰败。
为什么呢?在当地人看来,就是因为生源流失。可生源为什么会流失呢?他们认为都是因为别的地方在“抢学生”。
可实际上问题哪有那么简单?作者林小英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P县一中的衰落,生源流失只是结果,更深层的原因是县政府的失职。
其实,P县的教育经费并不少。按理说,这些钱本可以用来改善教学条件,激励师生,甚至提升县一中在家长和学生心目中的吸引力。
然而,这些经费用在哪里了呢?答案令人唏嘘——修校舍的工程、后勤的承包、教材的印刷,等等,这些有大量经费流动的项目,统统变成了教育部门干部家属的“生意”。
而本该用于激励的资金,例如发给优秀学生和老师的奖金,却常常“迟到”甚至“缺席”。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多媒体教学已成大势的今天,P县一中直到最近几年仍在使用传统的黑板和粉笔授课。

这意味着,本就稀缺的教育资源,在基层被挤压、被挪用,最终导致的是整个县域教育生态的恶化。
当然了,把锅全甩给体制也不公平。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同样是县城中学衰退的重要推手。
这些年,P县修了不少路,交通条件变好了,这本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便利”却加剧了大城市对县域资源的“虹吸效应”。优秀的学生、优秀的教师,像水一样不断往中心城市流去。
而留下来的,是一个“被抽空”的P县,以及一所逐渐失去竞争力的县中。
交通之路,变成了优秀学子的“出逃之路”。数据显示,2016年,P县中考成绩前100名学生中,只有15人选择留在本地读高中。这些数字冰冷又无情,但却真实地反映出教育资源流动的方向。
更可惜的事,P县的故事,不过是全国无数县城教育困境的一个缩影。
2.种瓜得豆:村小课堂实录
书里提到这样一个场景:在一个二年级的数学课上,老师给学生们看了一张画着20个气球的图片,然后带着学生们数气球。结果,数了整整六遍,学生们才把气球数对。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是这些学生智力有问题吗?当然不是。
老师一追问才发现,原来他们只是搞不明白,画里那些“被遮住一半”的气球也算是气球。
说白了,他们缺少对“画面逻辑”的基本认知,而这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从小接触的绘本、图画太少了,连最基本的“透视”概念都没见过。
相比之下,城里孩子生活在一个被丰富教育资源包围的环境里,他们很早就接触过各种图画书、拼图游戏、科教节目。
如此一来,农村孩子的“常识库”从小就比城市孩子少了一大截。可有些来自城市的年轻老师,社会经验不足,人生阅历不够,很容易就简单草率地把这些问题归结为孩子“笨”“不开窍”,甚至用偏见的眼光看待他们,忽略了这些孩子成长环境中的巨大差距。
除此之外,当大城市里的孩子们觉得被管得太严、不堪重负的时候,乡村孩子孩子却缺乏家庭的管教。

这些孩子从小到大最大的问题,不是“听不懂”或者“学不会”,而是压根儿就不在座位上待着。
坐一会儿就没有坐相,老师还在台上,他就旁若无人地离开座位乱走,甚至直接跑到操场甚至是学校外面玩耍。你说老师能怎么办?
理论上讲,这反映了家庭给孩子灌输的“初始习性”,和学校试图教会他们的行为习惯之间的冲突。
但村小的老师们哪懂这些理论?他们也没精力管这么多。对他们来说,只要孩子不出事,安全地待到下课,就算是“谢天谢地”了。至于课堂上还能学到多少东西,那就看各人的造化了。
而且,老师的工作远不止教书这么简单。村小的老师还要花大量时间纠正学生的生活习惯,比如督促他们洗头、洗澡、换衣服。
一个老师每天不仅要管教,还要操心这么多琐事,哪还有心思专注在教学上?
在这样的环境里,村小的课堂最终变成了一场“种瓜得豆”的表演。面对这么多“花样百出”的学生,老师只能用一种最简单、最省力的教学方式——以纪律为中心,把教学内容机械化处理。
比如,老师说出前半句,学生接上后半句,整个课堂就像一场“填空游戏”。这种教学方式看似维持了课堂秩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培养的其实是学生的“察言观色”能力,也就是说,他们学会了等老师给出提示,再想下一步怎么回答,而不是独立思考。
这样的学习方式,让这些孩子在潜移默化中放弃了成为“教育佼佼者”的可能。
他们的教育轨迹几乎是被“设定”好的:出生在乡村,长在乡村,短暂地在县中接受一些有限的教育,然后回到乡村,继续重复父辈的生活。
在课堂之外,他们的人生好像也早就被画好了圈,只是在这个圈里打转罢了。
3.学校的正事与杂事:教职人员的多重使命
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但现实中学校的功能,其实早就被层层加码了。
比如,政府搞禁毒宣传、普法教育,学校就成了主要阵地。毕竟青少年都在这儿学习生活,这安排顺理成章。再比如,孩子上学放学,人流量大,保证安全也成了学校的责任,这好像也没毛病。
但这无数个“没毛病”堆在一起,就成了问题。
有个新闻,一个高三的班主任,收到一份关于整治不文明交通行为的通知。家长骑电动车接送孩子时如果没带头盔,就通报批评老师。这事儿也得学校来管,那交警是干啥去了?如果啥事都让学校兜着,那学校的活儿岂不是干不完?
可现实中,很多县里的学校真就是这样。
一位县中的校长说得直接:“凡是社会上搞不定的事,好像学校特别神,能搞定。”这种“万能神话”背后的代价就是,学校不得不接手越来越多的“杂事”。
在校长们眼里,这些“杂事”是啥呢?简单说,就是外面硬塞给学校的活儿,跟教学关系不大,却占用大量时间和精力。而所谓“正事”,当然就是教书育人。
但现实哪有这么泾渭分明的事儿,有些工作游走在“杂事”和“正事”之间,问题就出在这些灰色地带上。

比如“控辍保学”政策,这本来是脱贫攻坚的一部分,要求做到“零辍学”。听起来很好,但具体执行起来,教育局发现,还得靠学校出面才行。
毕竟,校长和老师去做家访,比行政部门直接去沟通要有效得多。结果,这工作就顺理成章地落在学校身上了。
问题是,“零辍学”对一个县城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了应付检查,学校的教职工花了不少时间跑腿、填表、陪同谈话。更别提随之而来的扶贫任务了。
扶贫攻坚任务对每个事业单位来说都不陌生,学校更是重头戏。一般的扶贫模式是“包村”,学校的干部需要对接贫困户。
那些分散在交通不便的村庄的农户,走访一次就要花上一整天。而在村委会里,你还能看到两个负责扶贫数据录入的老师。
他们干的活本该是村干部的事儿,就因为村干部不会用电脑和操作软件,所以老师们不得不接手。这样的“杂事”数不胜数,占用的不仅是时间,更是教职工的精力,听上去全是负担。
不过,要说这些事儿完全没价值,也不公平。教育本身就是和人密切相关的,县里的教育更是深嵌在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中。
要完全脱离这些,去追求所谓的“专业化”或“职业化”,既不现实,也没必要。学校扎根社区,承接一些行政任务,确实能让整个系统的运转更高效。
只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在的教育体系是“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所有社会边缘事务最终都会压到学校头上。
教学时间被挤占,家长和老师的沟通机会减少,久而久之,学校就会失去它作为教育场所的核心价值,沦为一个“孩子托管中心”。
甚至,有人把学校比作流水线工厂。那这样的学校还有教育的意义吗?
诚然,县城学校的问题远不止这些,想了解更多的朋友,不妨自己找本书来看看。
无论是县中的孩子,还是城市里的孩子,他们都不只是某个家庭的责任,更是我们这个社会共同的未来。星星之火,终会燎原。但前提是,这些星火需要被守护,被呵护,更需要风助火势。
教育这条路很长,但如果每一个人都愿意为“我们的孩子”多迈一步,那这条路,终究能走得更远。
微信内容编辑:凉三
监制:翻墙陈
配图:网络,侵权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