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比茅台还赚钱,学费越涨越没人交,民办高校还能撑多久?
十年前,最暴利的生意,不是炒房,也不是卖茅台,而是开一所民办大学。
有人形容:一旦校门建起来,学费就像水龙头一样哗哗流进来。
那时候,广东某高校的财务总监对外吹嘘过一句话:“只要招满一届,就等于收回了建校成本。”

然而,2025年的招生季,一幕讽刺的场景出现了。
云南连续六次征集志愿,广西本科补录干脆取消了分数线,甚至理论上0分也能上本科。
那些曾经利润率堪比茅台的学校,如今却连学生都招不满。
为什么过去的“印钞机”,今天突然失灵了?
01
回顾过去二十年,中国民办高校的崛起几乎是时代红利的产物。
2000年以后,本科扩招加快,很多省份的重点大学依然一位难求。
在这种背景下,民办本科院校迅速填补了需求缺口。
2010年前后,全国高考生人数徘徊在950万上下,但本科录取率不足40%。
这意味着,只要开出一个“本科”的招牌,就能吸引成千上万的家长。
以江西应用科技学院为例,这所成立不久的学校在2018年就实现了73%的毛利率。
也就是说,每收100块学费,73块进了口袋。要知道,同年贵州茅台的毛利率也不过76%左右。

更直观的例子是山西通才教育。
2020年,这所院校的净利润是1.43亿元,净利率高达53%。
换句话说,每挣两块钱,就有一块是纯利润。放在制造业,这样的数字简直不可想象。
而在学生眼里,这些学校的课程设置往往是文史类套餐,市场营销、国际贸易、工商管理。
听上去高大上,实际上就是几张课桌、一摞教材就能凑合开课。
实验设备昂贵?实验楼难维护?没必要。
轻轻松松招满几千人,账面上就是上亿营收。
02
当学校不再只是办学的场所,而是被视为现金流资产,故事就变了味。
2017年之后,一大批民办教育集团在港股上市。
比如上海建桥教育集团,上市募集的资金里,超过三分之一是用来收购其他学校的。
中教控股更是资本市场的明星。
2018到2021年,它花了近96亿,收购了10所高校。到今天,它旗下已经拥有14所学校、28万学生。

要知道,北京大学在校生不过4万出头。
换句话说,中教控股一个集团的学生规模,能顶上好几个北大。
但这些钱,并没有主要流向实验室和师资培养。
更多的投入是买地建楼,把宿舍扩成“摇钱树”。
宿舍越多,住宿费越高,账面数字越漂亮。
至于教学质量是否跟得上,并不在优先考虑的清单里。
资本逐利的逻辑下,民办高校更像房地产公司招生和盖楼就等于盈利。
03
拐点出现在就业市场。
2025年的中国,大学生就业的难度已经不比当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轻松。
研究生扩招、本科批量化、技能型岗位增多,让单纯的本科学历变得越来越廉价。
广东白云学院去年发生的一幕堪称典型,1477名新生在录取后集体放弃入学。
原因很简单,学费高、就业差。
家长算了一笔账:四年下来学费住宿费加起来十几万,毕业后孩子找不到对口工作,反而背上了高价文凭的标签。

一些学校为了补窟窿,反而大幅涨价。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一年学费6.8万元,几乎直逼留学费用。
东莞城市学院也把学费抬到3.4万元一年。
可问题是,越涨价,越没人愿意掏钱。
更惨的是,有的学校连基本运转都维持不下去。
大连某民办高校被曝停发工资,学校账户甚至被法院冻结。
可即便如此,校方仍要求学生在十天内交齐新学期学费。
这样的场景,彻底击穿了社会对“民办本科”的信任感。
04
民办高校的困境,并不是某几所学校倒霉,而是整个模式走到了尽头。
首先,人口红利正在消退。
虽然高考人数依然在千万级,但增长趋缓,分流严重。
职业教育、海外留学、专科扩招,都在瓜分生源。
其次,就业导向彻底改变。
互联网行业裁员潮、房地产行业收缩,让年轻人对本科文凭的信任感下降。
许多人宁可学技能、考证书,也不愿花大钱买一个无用的学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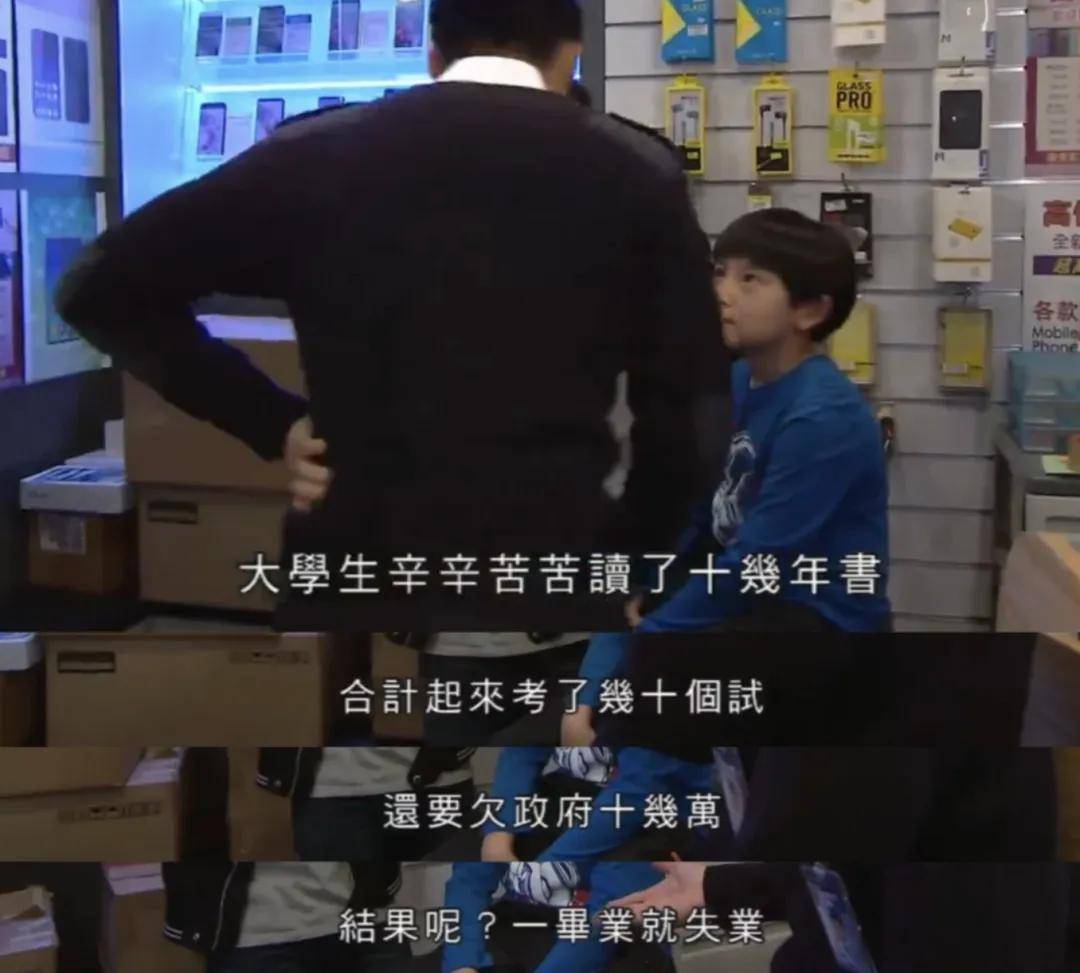
最后,资本逐利透支了行业信誉。
上市公司频繁并购、追求财务报表的漂亮数字,却忽略了最根本的教学质量和学生未来。
这种短视,让原本可能长期存在的市场,变成了一场资本的盛宴和清算。
正如一位教育学者所言:“民办高校的衰败,并不是教育的失败,而是资本主导教育的失败。”
05
从暴利神话到今天的危机,民办高校走完了一条快速起落的曲线。
它的兴盛依赖于人口扩张和学历焦虑,它的衰败则源于就业压力和教育价值回归。
教育,本应是一项慢工出细活的事业。
但当它被资本裹挟,变成了财务表上的利润指标,注定会有今天的结局。

这场崩塌,给中国教育留下的启示是,教育不能被当成套利游戏。
短期可以靠扩招、靠盖楼、靠并购撑起神话,但长期的根基,永远在于教学质量和学生的真实竞争力。
资本神话已经破灭,可真正的教育,才刚刚开始回归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