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四年的难关,我这样陪孩子走过
邮箱:tbeducation@daznet.cn
文丨金慧 编丨Amber
写在前面:
指责孩子,对他发火前,先想一想,其实没有天大的事,我们要调整好心态,毕竟孩子只是孩子,作为父母我们可以更强大一点。请看这篇来自一位妈妈「开窍」的心路历程:
看着时间慢慢接近14:00,感觉到心跳的加速,点开电脑里早已加入收藏夹的教育考试院网址,颤抖着双手把报名号敲进去,页面赫然跳出了中考各科成绩和总分。
和这个分数一起落地的是预初一年和初中三年来的焦虑和不安,也是又一次证明自己的方式。
小学时的yq孩子停摆了3年,空中课堂形同虚设,而电子产品再也无法离手。
初中了,让我隐隐有些担忧的是他沉浸在二次元中,周末和假期天天抱着IPAD,除了有时和我聊几句外,几乎不和任何人交流。性格孤僻这个词是我那段时间听得最多的别人对他的评价。
但只有我知道他内心的敏感和细腻,被二次元作品里的人物以最具象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让他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有次他说:
“如果发生战争,我会去参军,然后冲到炮火的最前线,随着一声爆炸,我可以进入我的二次元世界。”
虽然纠正了他的言语,但我内心开始担忧他的心理状态,学业上不敢给他任何压力,电子产品也是由他自己安排。但成绩起起伏伏也让他的情绪逐渐开始更不稳定,进入二次元的幻想时常挂在嘴边。

基于他这样的状态,我建议他试试哲学课,一开始他特别反感,坚决不肯上。我妥协道:“要么这样,咱先上一次看看,如果实在不喜欢就算了。”
第一次课,我坐在他身边,原本无精打采的状态被小爱老师不寻常的开场自我介绍一下激了个哆嗦,转头看向我,张着嘴,抱着头,直喊着:“怎么办?怎么办?”……整堂课感觉他全身的细胞都活了,最后他欣然地继续学着,只是后面的课,不再允许我旁听了。
这样忙忙碌碌地过完了整个七年级,成绩和所花的精力也是成正比的,不好也不坏,平平常常。
要说在学习上没有焦虑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我认同景芳老师的观点:“先联结自己,联结学习,再向上生长,最后才是成绩的结果。”
初一升初二的暑假,他和几个小伙伴相约天天去公园打篮球。被晒得黝黑的皮肤和猛涨的身高都彰显着青春期活力。
胖小伙变成了瘦高个,但烦恼也是有的:孩子照镜子的时间和频次变多了,不停地摆弄他的头发,头发很长了也不肯去理发,他总说这个长度刚好是最好看的时候。
在我看来,刘海遮住眼睛,两边鬓角炸在耳朵边,谈不上什么好看。提醒他去理发,在不情不愿中理完发后,总是以长久的冷脸来报复我的管控。

后来我放过自己,不再催,但家里总有人受不了,回家看见孩子留下两行热泪,原来是老爸逼他把心爱的遮眼长发理了,让他觉得自己没脸见人。
但实际上我看到的是一个元气小伙,没人能理解他此刻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也理解不了,但他的伤心也是实实在在的。
这样的拉扯一直持续了很久,而我能做的只有等待。
我发现相对发型失意,在篮球场自由挥洒汗水,能让他忘记发型的烦恼,而他对篮球的痴迷从这个夏天开始更胜一筹了。
八年级开学他加入了校篮球队,同时又组建了班级的篮球队,队员都是他自己挑选的,训练也是他负责,目标是拿到本年度的班赛冠军。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体育课、午休、大课间,抓紧每分每秒打球。
每天回家和我聊的都是篮球:从班级队友的训练到学校的篮球队到NBA球星,甚至走在路上也会突然神经质地空手投个篮或者转个向。再后来他觉得需要更专业的教练,于是老母亲开始找相对专业的篮球培训机构。
每周要训练两次,其中一次还在周一晚上7点到9点。这个时间点是:这不应该是写作业的时间吗?看出我的犹豫,他向我保证会安排好时间。
面对他坚定的热爱,我妥协了,按娃他爸的说法,我总是惯着他。
有次班主任突然找到我,说想问问孩子被选进了实验班为什么不愿意去?我都不知道有这个事情,他振振有词地说了半天,实验班要在周一放学后多上一节课,而他要去打篮球。
我又妥协了,帮着他打掩护,给老师列出了不去的1,2,3条理由(其实都是借口),最后老师回复:好的。
篮球是打得风生水起,在训练机构里一位来自立陶宛的年轻教练用心、踏实、有激情,还有和他同款对篮球痴迷的队友,那段时间那个机构成了他的精神家园:有志同道合的伙伴、有欣赏他的专业教练。
每次训练我都在场边的观众席上看这些热爱篮球的孩子们在训练场上奋力地奔跑,灵活地过人,默契地传球、投篮,一切行云流水,与平时在家写作业的精神状态截然不同。

篮球虽好,但烦恼随之而来,他开始频繁地受伤,最严重的一次上篮的时候被垫脚了,随着一声惨叫而倒地。之后的好几周都无法正常行走,但即使这样,他还要参加教练的战术课。
在场边看着伙伴们打球,旁边一位孩子的妈妈看不下去了,和我说:“你也真是的,现在时间这么紧张,不打球还带他特地跑过来看别人打。”哎~我只能无奈地苦笑。
这段时间,周围的同事、朋友、甚至家里的老人都看不下去了,不停地提醒我,这样松散可不行啊!得让他去上补习班了!
我当时计算了一下他的空余时间,上补习班再加上补习的作业,就意味着篮球或创意写作课得停下,篮球他是绝对不会停的,而写作课带给他的收获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
第一学期的课程结束后需要提交一篇作品鉴赏,他第一次以创作者的视角去分析二次元作品中的人物、情节等,在二刷三刷的时候这些专业视角的分析每次都让他有全新的收获。
而这样的鉴赏能力也自然地迁移到了对其他文学作品的理解上。于是和他商量,结果可想而知,他要继续上篮球和文学写作课。
另外不幸的是,这学期他特别喜欢的数学老师被调走了,万分不舍却又无可奈何。
对新老师上课的不适应、数学难度陡然上升、大部分心思都花在篮球上,所有这些因素的叠加导致了他的数学成绩逐渐下滑,引用他自己文章里的一段话:
“九十分的成绩变成了七十分,我拖着焦虑和绝望,被不甘和苦恼拉着在七十分的荒原疯狂着扑向一丝八十分的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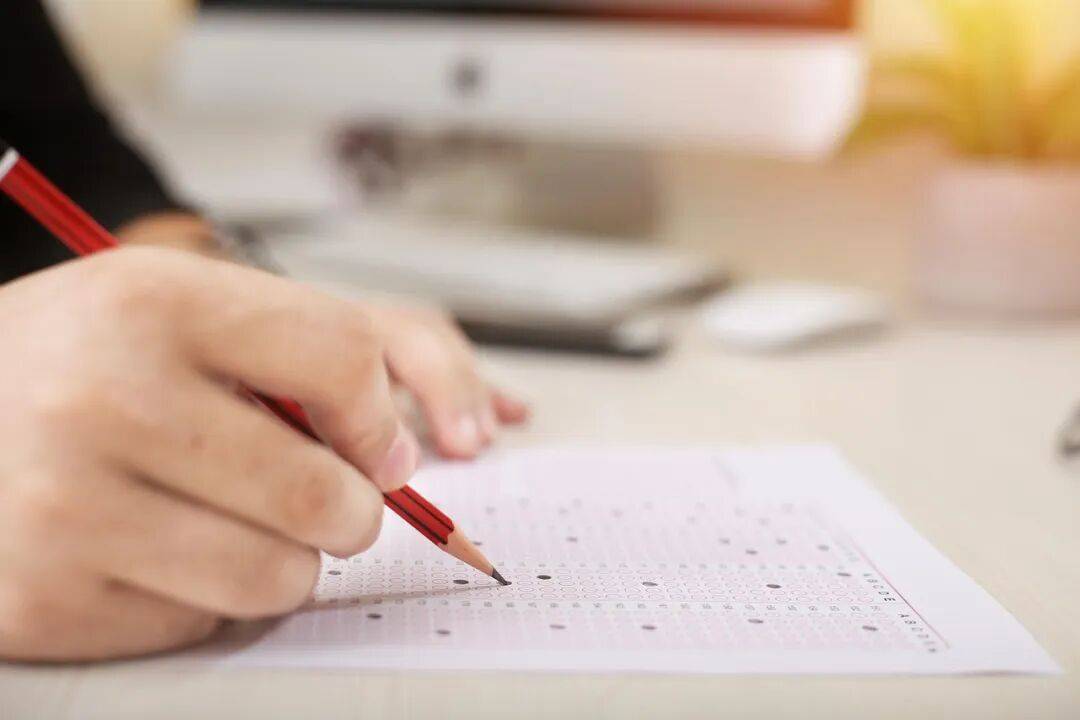
而对每一次的下滑,我鼓励的话总显得那么苍白。
这些压力他都得自己扛着,抗到第一学期结束,期末成绩出来,排名已跌出前30%。第二学期分班,他曾经放弃的实验班,此刻早已没有了他的位置。
学校的家长会是1对1的,班主任神色凝重地说:“以您家孩子现在的认知水平,如果他就认准了篮球比学习重要,那您就得降低预期,接受他去一个一般的高中或者职校。”
班主任的话在我脑海里回荡了好几天,我一直在问自己能否接受这个结局?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要不体制外?创新学校?或者中本贯通?
一番思考后,行动力超强的我马上开始上网查各种选择的利弊,关注各类学校的公众号,看各种评论,体制外和创新学校最终的出口都是出国留学,这条路虽好但却需要卖房卖车倾尽所有才能够到,不现实。
最后我锁定了一所中本贯通的学校,继续深入地了解,但网上的信息琳琅满目,真假难辨。我决定实地探查:下班后蹲在校门口,和保安聊天,拦截正出门的学生详细询问,参加学校的开放日,和在读和已毕业的学生深度交流。
确定真的适合自家孩子后,回去和他商量,结果人回了一句:“我还没开始拼搏,你凭什么就认为我考不上市重!”我傻掉了,忙活了近一个月整了个寂寞。
但决心和行动间似乎又差了不少距离,我看到的他的状态似乎和之前没有什么不同,大部分的空余时间还是在研究篮球,然而作为一名要面对中考的学生,学习成绩是永远都绕不过去的,最困扰他的是数学,让每次的月考成了他的劫难。
看着数学试卷上那么多的红叉和空白,他抱着我嚎啕大哭:“妈妈,怎么办啊~我很认真地听课了,也很认真地订正错题了,为什么每次考试都那么多不会做啊~”
我有些无措,不知道如何安慰此刻伤心的孩子。过了许久,我说要不咱也去外面补课吧?平复了心情的他又一次拒绝了,而我也没有坚持。
可是这样情绪奔溃决堤的次数和程度一次大过一次。他的状态成了全家人的晴雨表。每天晚上他进家门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先看他的脸色,见他神色如常,大家心里都长舒一口气,见他面色土灰,大家说话都小心翼翼。
有好几次,他进门、坐下、吃饭、走人,全程低着头不和任何人说话。也有好几次等他吃晚饭等到7点多还没回来,每个人都焦虑地重复着一句话:“咋还没回来?”
后面的话大家很默契地都没有说出口:会不会出什么事。但还好,每次都能看到他低着头、疲惫地进门。
他也在努力地调整着自己:有时候关着门疯狂地弹琴,有时候出去酣畅淋漓地打球,有时候关闭周围的一切沉浸地写作……
这些他坚持下来的兴趣现在竟成了他宣泄和表达情绪的方式。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多久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痛苦太容易被遗忘,但熬着~熬着~的心境一直在脑海中浮现。
而在我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他发现这几次考试开始止跌了,这样的信号给了他极大的信心。
他说:“妈妈,咱不着急,先稳住。而且今年我还有最后一个心愿,就是要带领我们班篮球队拿到班赛冠军。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接下来他确实比以前努力了,只是跌入低谷想爬起来谈何容易。但好在现在的他心境已然不同,整个人没有了之前的那种颓势,眼里又有神了,笑容也多了。
期末的颁奖典礼上,他以骨盆受伤的代价拿到了班赛冠军和MVP,篮球让他证明了自己。

初二升初三的暑假,他的篮球教练回国了,伙伴也因为学业压力退出了训练,他在一篇文中写道:“原来深藏在心中的从来都是那群伴在身边的人。”
于是他也退出了篮球训练,并主动提出要去外面补习数学,我调侃道:“你这是给我省了好多补习费啊!”
补课之余,抽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参加了暑期写作营——这个让他至今都难忘的营地,松弛、欢乐、自由的环境让他沉浸式创作,成就感满满。
回来后他说:“好像在游戏里抽到了一张体验卡,有了一次完全不一样的神奇经历。”
因为我们那时正在云南旅游,经他强烈要求,又回到了那个营地,带着我们重温他的故地,曾经烧烤的小院此刻冷冷清清,他摇头感叹物是人非;又去了他们曾经晚饭后散步、看晚霞的湖边,此刻湖中的荷花静静盛开着,他指着周围整洁的小道回忆着那几天的欢乐……初二的暑假就这样在美好的回忆中结束了。
初三一上来又分班了,他险进实验2班,由此遇到了用他现在的话说是“救自己命的”老师们。此后和我讨论时的开场不再是篮球,而是“你知道今天Y老师是怎么给我们上物理课的么……”每天滔滔不绝地给我上物理课。
我从他的口中也见识到了原来跨学科的学习在公办学校的大课堂里也可以发生,原来真的有老师可以兼顾素质教育和应试需求。从上Y老师的第一堂课开始,他就成为了孩子的新偶像。
对于数学老师,一开始给他的印象特别不好:讲课速度快,严抓订正,学习态度不好的从实验班里踢出去。有些学生为了不上她的课宁愿放弃实验班。一周下来,我家娃极度不适,但为了能上物理老师的课,他就忍着。
一对一家长会的时候我把这个情况和班主任交流了一下,她说数学老师非常优秀,让孩子适应一段时间就好了。
事实证明她是对的,有次由于学校的临时安排,原来的数学老师又给他们上了几节课,他回来说:“这两天的数学课就是养老局,讲得太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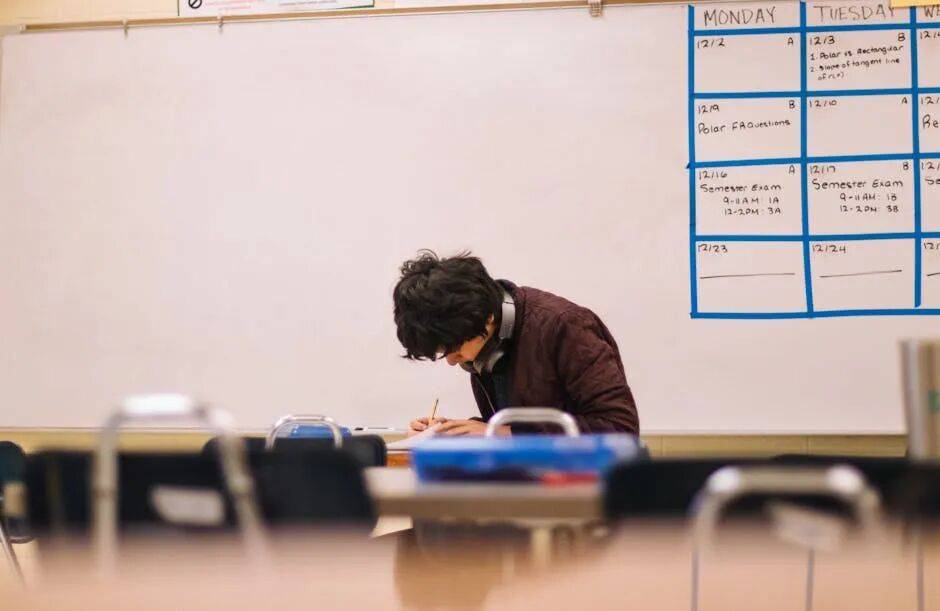
尽管他自己感觉数学思维水平确实提升了,但每次考试分数一直维持在110+,他太需要一次考试来证明自己。于是每天晚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和数学较劲,这直接导致他擅长的文科全线下跌,而数学也一直没有太大的起色。
在二模考的时候这种煎熬达到了顶峰,前方一片黑暗,未来一切迷茫。那天深夜和往常一样做完作业后出来洗漱,又回他的房间,不久,我听到从他房间发出的低低的抽泣声,轻轻推开卧室的门,黑暗中借着透光的窗帘看到他蜷缩在床边哭泣:“只剩一个月的时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以后不要啃老,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
他的状态让我无限自责:“对不起,你现在面临的困境,妈妈要负主要责任……”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黑暗中他感觉到我也在哭泣,用手摸了摸我的脸,满手都是泪,他立刻止住哭,用平静的语气安慰我:“我们都要相信,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
我猛然意识到不能让他再耗费额外的精力来消耗我的负面情绪。然而他接下来的话又让我错愕:“后面你不要把弟弟逼得太紧~”。
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他完成了中考体育、英语听说、理化操作。回来的路上,他用羡慕的眼神望着从容走在前面的同班学霸,对我说:“这是个大佬。”我听出了他的自卑:“大佬咋啦?这么消瘦,我看还是你更健康更阳光。”他笑笑不语。
中考前的几天,学校安排自己在家复习。六月的上海总下着淅淅沥沥的雨,潮湿的空气夹杂着考前的焦虑和分离的忧伤,他每天晚上拉着我在小区里散步,和我细说在学校的最后一天放学,和好朋友在路口分别时的情景,如同这四年来的每一天放学一样平淡,只是这次是最后一次,而他的心境犹如这连绵不绝的雨天一样潮湿。
我每天晚上都陪着他出来散步,话题也逐渐发散,他会对路灯下细雨婆娑的树叶感慨一番,也会透过楼间的空隙看到不一样的街景而驻足拍照……这四天的休整让他慢慢沉静了下来。
考试前一天,学校办了一场用心的誓师会,孩子带回来一堆祝福礼物,亢奋地说:“氛围拉满,已进入状态,只等明天开考了~”考试的两天都下着倾盆大雨,加剧了我在家等待的焦虑心情。
考完回来后,他说:“这次真的尽力了,是我四年所有的考试中做得最认真的一次。”之后的一周他重拾了之前一直想学又没时间学的吉他;和好友一起玩密逃、滨江骑行……没多久他就加入了初升高的补习大军。去年的我还在吐槽好友,孩子中考完还不给喘息的时间,如今的我竟然如此自然地与她如出一辙。

填志愿的那几天,我把上海高中学校的清单以及往年的分数线给他看,他筛选了自己估分分数段内的学校,又去网上查这些学校的“气质”,果断地放弃了那些鸡血的学校,再三权衡后选择了契合自己个性的学校,志愿里的每一所学校他都去网上反复看学长们的反馈。
自己选择的路,才能坚定地走下去。最后到区(上海的中考志愿依次分为自招、到区、到校和统招),被一所老牌中游市重点录取了。
用细细碎碎的笔墨记录孩子起起伏伏的四年光阴,是回忆也是勉励。我问他如果可以重来会不会早点自卷。他说还是会和现在一样的选择,因为这是他的青春;他说他是个很自我封闭的人,庆幸能遇见我,让他从那壳中走出来。
其实我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帮到他的,也许是自己从小的不自信所以不停地学习,也许是天生的心软所以无法做到控制,也许是内心一直保持着一颗童心所以可以共情。
当一个妈妈“开窍”,正视自己能陪伴着孩子成长,而孩子的成长也是妈妈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和解的过程时,在这场共同成长的旅程中,你和孩子,都将是彼此最珍贵的礼物。
K12 成长与教育社区
追踪前沿资讯 洞察成长规律
挖掘充满温度的故事 探索融合世界的教育
妈妈一旦开窍,就很难再对孩子发脾气了
